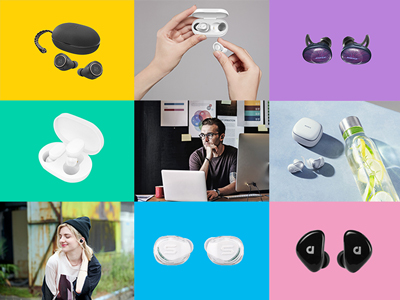文/陈远
这篇文章,所述内容根据2013年所拍电影《萧红》。故事情节是否真实?我未曾探究。——作者自题
作家萧红在呼兰乡下的日子过得很苦。只有祖父对她很好,祖父教她读诗词,常常陪她到野外玩耍。祖父对她说:“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所以,当萧红去哈尔滨读书时,最牵挂的就是祖父了。然而,萧红还没有毕业,祖父就去世了。萧红心中的支柱轰然倒塌,祸不单行的是,父母(其生母已在萧红九岁时死去)不让她再回哈尔滨,并迫她嫁给一户姓汪的人家。萧红坚决反抗,一走了之。那时,她还不足二十岁。
长大了就好吗?我们看看萧红此后的遭遇。1931年初,萧红到了北平,靠表哥支持,她进了师大女附中,但表哥给家里逼回去之后,萧红就连房租都无法缴交。正当山穷水尽时,那位姓汪的竟找到萧红住处。不知道是因为萧红已无路可走,抑或因为姓汪的连工作都抛掉而来追她所以使她忽然生发感动之情,萧红与姓汪的同居了。即使,萧红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即使,姓汪的并非萧红所期待的人。同一年,姓汪的钱花光了,他带着萧红回到哈尔滨。那时,双方家庭已把婚约解除,萧红与姓汪的只能住在东兴顺旅馆。在萧红怀孕后,姓汪的竟找了个借口溜走。房东不甘心房租等没能收到,说要等萧红把孩子生下来后,就把萧红卖到道外妓院。
如果不是《国际协报》记者萧军,萧红此后不堪设想。萧红对萧军细述苦楚,她并说:“早知如此下场,我何必抗争,何必出走!”真的,倘若萧红不抗争、不出走,听听话话地跟姓汪的成婚,萧红的故事或许改写。但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姓汪的对萧红动辄打骂,他把萧红留作为“人质”,实质是遗弃萧红。
正如萧红在最绝望的时候见到姓汪的一样,萧红也是在最绝望的时候见到萧军。 所不同的是,萧红对姓汪的没有感觉,却为萧军的文武双全、朴素坦诚所动情。萧红说“从天而降的萧军,给我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还让我获得梦幻般的爱情……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见他和等待见他。”
在电影中,萧红、萧军最感人的一幕是:洪水来了,挺着大肚子的萧红离开被禁锢的阁楼去找萧军,正在她彷徨四顾时,正涉水赶来的萧军一眼瞥见坐在艇上的萧红。四目对视了,萧红赶快挣扎着从艇上下来向萧军跑去,萧军也赶快向萧红奔来。患难相交的两个人终于拥抱在一起了:“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来晚了。”“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不分开了。”……
萧红生下姓汪的孩子却送给了老家在沈阳的一户人家,那是可以理解的。在那颠沛流离的岁月,如果不是已经停刊的《国际协报》主编赞助了5元钱而住进欧罗巴旅馆,萧红、萧军便可能流落街头。在这种恶劣的情势下,他俩怎能养小孩呢?
因为有了萧军,萧红以为:“无论如何,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但是,“萧军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他很讨女人喜欢,也很喜欢女人。”萧军与冯家姐姐有染,萧红“不愿面对”,“内心深处却开始积聚忧伤。”
宪兵天天抓人,1934年初夏,感到危险的萧军带着萧红离开哈尔滨,先到青岛后到上海。他们给鲁迅先生写信,后来甚至与鲁迅先生见面。他们得到鲁迅的帮助,先后出版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本来,生活应该可以逐渐安定,但是,萧红与萧军的感情裂缝却越来越深。鲁迅太太许广平对萧红说:“一个萧军就让你万念俱灰了。”“你应该让自己走出他的目光,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鲁迅也开导萧红:“你在感情上太过投入,性格又偏倔强。”萧红回应道:“遇到萧军到底是我的幸运,还是我的不幸?喜欢他,但不能拥有他;恨他,又离不开他”……
1936年7月,为了躲避眼前和萧军的烦恼,萧红到日本去。但在日本,萧红却很想念萧军,她甚至把对萧军的一切向她和萧军的一位朋友的妻子阿虚和盘托出。萧红在日本一边写作一边学日语,但鲁迅的突然辞世,却让萧红匆匆赶回上海。很快,萧红大受刺激地知道阿虚怀了萧军的孩子却做了人流手术。
到了这个地步,萧红仍然走不出萧军的那个世界。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要打到上海了。萧红与萧军,还有另一作家端木蕻良一起逃难到山西临汾。就在此时,萧红有了萧军的骨肉。日子艰难,他们三人相互照应,有时迫不得已地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终于有一天,萧红与萧军有一段对话:“我可能不再爱你了。”“你对我有误解,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无情无义的。”“是我爱上了别人。”萧军心中有数,接着说,“他不适合你。”……
到了这种田地,萧红与萧军的关系本应降下帷幕了,但继而的一个场面却又令人莫名。火车就要开了,萧红站在车上巴望着,忽然,只见萧军拼力地向火车奔来,这就瞬间引起萧红的回忆,水中相见的那一幕再现。萧军跑到火车旁了,他把手中的两只梨子递给萧红。萧红与萧军吻别,接着哭得伤心;萧军为她擦拭泪水,也在哭着。火车开了,萧军跟着火车在跑,他与萧红招手,最后剩下的只是萧军茫然望着火车远去的特写……
“他不适合你。”在某种程度上,萧军说得对。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在武汉结婚,“但热恋没有维持多久,我们的感情就陷入僵局。”武汉沦陷,端木一个人先去了重庆,就在萧红独自前往重庆的途中,她生下了没几天就夭折的萧军的孩子。可怜的萧红深深感到:“和萧军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端木“不是一个能够担当的人”。电影中有组镜头令人看着压抑:1941年1月,萧红与端木到了香港,端木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前头走着,萧红却不胜重负地拿着行李在后头跟着。终于忍不住了,萧红满腹怨恨地把行李扔到地上……
萧红身体本来不好,到了香港,情况更糟。轰炸越来越近,萧红已病得走不动了。端木与另一作家骆宾基陪伴萧红走了最后的黯淡时光。他俩把萧红送到医院,又在护士都走光而只剩下几位值班医生的医院里照顾萧红。国难当头,又为顽疾所缠,萧红是不幸倍加。
一个晚上,萧红躺在床上似睡着了,骆宾基坐在椅子上朗读着萧红的《呼兰河传》:“……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下流的时候,使看到河灯的人们,内心无由的来了空虚,那河灯到底要漂到哪里去?”萧红浮想连翩,她对骆宾基说:“……刚才我梦见家乡的河灯了。河灯漂过,我看见奥菲利亚浮在水面上,我看清她那张脸,她顺着河灯漂过,她并没有沉下去,越漂越远,越漂越远,不见了。”又一夜,骆宾基回九龙去了,萧红对端木说:“……我有几句话对你说,不要让人随意删改我的作品,版权都由你负责。日后你回哈尔滨,帮我找一下我的女儿,收养记录在医院里。我们把《呼兰河传》的版税送给小骆吧!送一些我的骨灰到鲁迅先生的墓前,我想陪着他。”这无疑是萧红遗言。但临末还有啜泣着的端木与萧红的对话:“你会好起来的。”但泪流披面的萧红不说“早知如此下场,我何必抗争,何必出走!”,却说“我想回家。”接连的画面都是萧红儿时情景的回顾:她在前头走着,祖父在后头追着,还有祖父的声音在空旷中萦绕着:“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