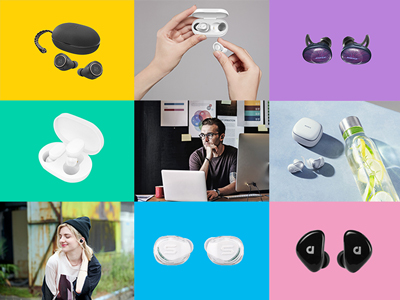刘欢接受早报专访 谈真人秀、创作和音乐品味
刘欢在音乐上从未给自己划分界限,同时也一直是隐在音乐背后的人,和这个圈子始终保持疏离。
很久以来,刘欢几乎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在大陆歌坛的流行风向中屹立不倒,走红于“西北风”盛行、大陆摇滚崛起、港台歌手涌入、校园民谣,以及“94新生代歌手”(孙悦、杨钰莹、毛宁)的时代,却直到所有与他同时代的浪潮都已平息的今天亦能唱一首歌是一首歌。
《好汉歌》的率性草莽,《千万次的问》的大气坚定,《从头再来》的真挚温暖,皆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亦因为刘欢的演绎而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浪潮中,听到如《从头再来》这样的歌,是要落泪的。而近年的一部权力与情欲交织的《甄嬛传》,本是中国文化中最勾人去看又最龌龊不堪的内容,却因为他写的那些古雅洁净的歌而有了怀古的意味。

之所以成为全中国被大众接受程度最高的歌手(至少是之一),是因为早年热爱古典音乐的刘欢从未给自己划分界限。站得高,不拘泥,只为了做出最适合的音乐。比如他当年为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做音乐,“试过Rock(摇滚)一点的,也试过像Funky(放克)这种风格的,却最终决定中庸一点。片尾本来全部决定用弦乐,后来发现效果不好,还是选择了电声。”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刘欢一直是隐在音乐背后的人,和这个圈子始终保持疏离。他常年教授西方音乐史,不好抛头露面,以教师的身份和学校为荣。他身上一直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博学、温厚、较真,有坚守的准则。
采访刘欢,是因为他为《中国好歌曲》的学员涂议嘉制作了一张名为《我们是谁》的EP。涂议嘉,或者说《中国好歌曲》,是刘欢付出了很大心血的事情。一档真人秀能不能改变歌坛现状,不策划不表演的真人秀存在吗?刘欢相信真人秀的本质在“真”不在“秀”,点滴努力亦是努力。在这个问题上,记者和刘欢的看法不同。行文之间可见刘欢的真诚和执着。
以下的这篇邮件专访,字数较多。除了关于真人秀的话题,还涉及他对唱片工业和原创生态的看法、他的创作、音乐品味、对“魔岩三杰”时代的看法,以及“音乐本身远高于我的生活感受”的感悟。
有的回答很短,比如寥寥一句话:“算你看对了一次吧”。有的回答则洋洋洒洒,从《哥德堡变奏曲》、《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谈到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Dark Side of the Moon》,夹杂很多感叹号。见文如见人,就是这样一个刘欢。
小众不应成为堡垒,而应成为战舰
真人秀的核心在“真”不在“秀”
早报记者:《中国好歌曲》你几乎全程参与,尽心尽力。这样的努力是因为你真心觉得一个节目能够为中国原创音乐做出贡献吗?
刘欢:听您的话好像“做出贡献”是不大可能的?的确,凭一档电视节目想改变中国原创音乐的现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总比天天抱怨要好吧。这两年的电视秀既然推出一些歌手,就一定也能推出一些好歌,事实证明《中国好歌曲》也做到了。
早报记者:选秀舞台上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人/事是什么?

刘欢:我无法在这里给您列举什么人什么事,《好歌曲》给我的总的印象是总体水平超过了我的预期。在节目开录之前心里真的没有底,节目要求尽可能是新歌,什么样的人会来、能来,歌曲都是些什么形态,我们作为“导师”全然不知,两三场初选下来还真的不错,后面就比较有信心了。
早报记者: 你说过在选秀的舞台上,你的这一块是完全不受干预的。但是一个不经过策划,或者说完全没有表演和事先安排成分的节目是不会好看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你是怎么处理的?
刘欢:我很惊讶您也坚信选秀节目的好看是由于事先安排和表演,抱歉,我不认为是这样。电视真人秀的核心特色就是“真”,这也是这种电视节目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一些真名实姓的人在镜头前真实地展现自己,观众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以及对事情的反应看到他们真实的个性、真实的习惯,电视在这里要做的不是编排和导演,而是捕捉和选择,采取录播的方式就是为了甄选出真实中捕捉到的精彩的部分,我们在录制过程里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展现和精彩的碰撞是设计不出来的,也是演不出来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第一季好歌曲我队里的学员张岭选送作品参赛,节目组没人走漏风声,比赛前一个月我碰到他他自己也没说,所以当我推杆后认出他时我完全惊着了! 而这些是演不出来的。这才是真人秀的魅力!因为大家已经明白真人秀的真谛就都遵守规矩,以取得最好的节目效果。所谓设计,这就是!而不是像有些选秀节目甚至有些导演所做的事先安排好每个细节。我无法在这里给你一一列举。说到策划,那是指对整个节目进程和模式的规划,而不是对我们这些参与节目的真人的言行。我认为真正优秀的真人秀导演,应该具备把握整体模式框架走向和后期选择素材的能力,善于发现、捕捉甚至激发出真人的个性,而绝非掌控甚至主宰真人的一言一行。后者是愚蠢的。如果靠编排和表演,那大家去看电影电视剧好了。至于说到我的这块不受干预,我是指不要人为地干扰我个人对歌曲对声音的判断和选择。
早报记者: 对于《中国好歌曲》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创作的人未必能够很好地演绎自己的作品,你们在设计节目的时候是怎么考量的?
刘欢:是的,《中国好歌曲》的着眼点是在“唱作人”,这也是这十多年来乐坛的趋势,无论国内国外。的确,有很多优秀的词曲作者自己唱不好,甚至完全不能演唱,但一档电视节目很难“全聚合”,我们也正在考虑研发完全针对词曲作者的节目模式,那是下一步的事。
音乐大于生活就像在阴沟里仰望星空
早报记者: 你曾经解释过为什么自己的歌声里面没有很多“自己的心声”,而是纯粹的音乐。你是在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一点的?如今还是这样认为的吗?
刘欢:我并没有说过我没有“自己的心声”,我自己写自己唱怎么会没有我呢?我只是在创作的时候不强调我的自我表现。这是个关照点的问题,我也谈不上明白,我只能大概告诉您这个过程:当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接触到了西方的古典音乐,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些音乐在描述我,在表达我,表达我的快乐我的愁苦,甚至我的人生。后来我去了解它,分析它,不是分析它的情绪,而是它的构成,它是怎样在音乐上实现的。我慢慢发现它远远高于我的生活感受,又发现它甚至远远高于写那些伟大音乐的伟大的人的生活。当我发现《哥德堡变奏曲》的沉稳思辨和巴赫作为音乐仆人的身份那么不相符,当我发现莫扎特的《小夜曲》与他本人那么乖张的性格和窘迫的境遇那么不一致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些人的伟大之处,他们就是我们所谓的“仰望星空”的一族,他们懂得了自己的渺小和艺术的伟大,他们是所谓站在阴沟里仰望星空的人,而我可能只是因为所谓“愁苦”,只看着自己脚下的阴沟。后来,当我发现那么多捶胸顿足地表达自我踌躇彷徨痛苦的歌曲,在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序曲,或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前几小节面前就化为无形的时候,我更加相信音乐本身的说服力是超过所有文字注解出的所谓生命体验的,当我们听到Pink Floyd 的《Dark side of Moon》,Do So La #Fa,那让我们天眼洞开的音符的时候,谁问过Roger Waters(编注:Pink Floyd乐队前主创)的生活境遇呢?还是那句话——音乐至上。另外,我们很多时候理解华语音乐是依靠对歌词的理解;歌词只是文学辅助,而歌曲的核心元素还应该是音乐。试想一下,如果脱离了歌词,或者这些歌的歌词都变成多半人听不懂的外文,你还能从中感受到那些所谓的情感印记吗,还有那么多感动吗?
早报记者:从年轻时候热爱古典音乐,到后来唱“大歌”、创作、当音乐教授,你的音乐品味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早年打动你的音乐到现在依然如此?
刘欢:品味经常变化,总体是在拓展,越听越杂,一直没有变的是古典吧,但古典中也在变化,这几年喜欢这些,又几年就改了。
早报记者:你最近在听什么音乐?有没有哪一种音乐是确定不喜欢的?
刘欢:古典的方面又从巴洛克以前的转到法国的拉威尔或六人团的时期,还有爵士的,至于哪种确定不喜欢不好说,应该是那些听了前两小节就能知道后边的吧。
任何一种音乐都有权利被所有人听到
早报记者:很多音乐人都有过狂热、无序、冲动的岁月,然后趋于平静。但是你出道那么多年,我们看到的刘欢一直是个温厚沉静的人。是这样吗?
刘欢:算你看对了一次吧。
早报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大陆原创音乐繁荣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尝试不同的音乐,比如“魔岩三杰”那样的?你向往过树村那样的生活吗?
刘欢:“魔岩三杰”那样就是你认为的繁荣期的代表吗?看来您还是那种小众堡垒的捍卫者,作为一个乐迷这很好,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永作拥趸;但作为一个媒体人您要考虑一下,我记得“魔岩三杰”的时候没有“树村”,可现在“树村”的音乐人好像是把自己连同自己的乐迷们和外界隔离起来的。上一季《中国好歌曲》时我就发现,凡有所谓独立音乐人上电视都有点被当成叛徒的意味。只是因为欣赏趣味上或最多生活方式上的独特或不被大多数人接受就觉得要高人一等,这只能被看成是另一种固步自封。小众不应成为一个堡垒,而应当成为一艘战舰。任何一种音乐都有权利被所有人听到。至于“树村”那样的生活,我没有向往过。我有我的生活。